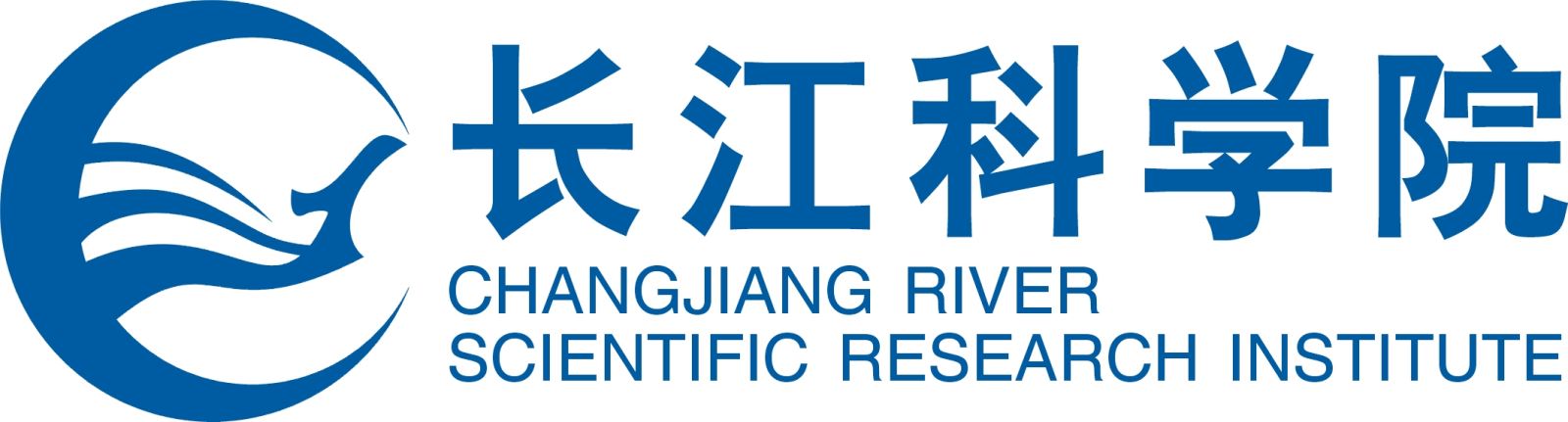|
| 首页 >> 会员活动 |
| 联合国电台采访王兆印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王兆印谈中国江河治理 |
| 作者: 来源: 清华大学 发布日期: 2011-08-18 |
|
联合国电台采访王兆印教授 2011年8月3日 清华大学教授王兆印谈中国江河治理
王兆印:获得爱因斯坦奖,我还是非常高兴的。我也收到了国内外友人的祝贺。因为这是首次把这个奖颁给中国人,实际上也是第一次颁给外国人,因为之前都是美国人获得。我觉得中国人获得这个奖还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在河流泥沙和生态方面作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我们的问题多,比如说我们有独一无二的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在抬升,它每年抬升2厘米,导致的河流问题远远比其他地方复杂,生态问题也相对更加复杂。 记者:研究泥沙运动规律对于环境保护有什么意义呢? 王兆印:泥沙,英文是erosion and sedimentation,实际上它本身就会对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侵蚀比较严重的地方,植被就比较容易受到破坏。有一个理论叫“植被侵蚀动力学”,用理论来预测,在一些地区,如果不控制侵蚀,植被是永远发育不起来的,光靠种树是不行的。另外,泥沙运动也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比如,高含沙水流会导致非常低的溶解氧,会把鱼杀死;重金属可以吸附在泥沙上,输送和沉积带来污染物质的转移。泥沙运动会对生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它可以创造栖息地和改变栖息地,所以泥沙研究对保护环境有很重要的意义。 记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什么要成立国际泥沙项目?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项目?又是怎么样开展工作的呢? 王兆印:主要是发现所有水利的项目都跟泥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泥沙又跟生态环境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加强合作和协调。其中有一个目标是对全球的泥沙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综合的认识。有这些要求,所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计划底下建立了这么一个项目。现在的总部是在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工作,比如说,对全球侵蚀量的估计,组织了一批人,把最要重要地区的人都组织起来,协调起来,把各家能够测到的数据资料统计了起来。但是这个工作没有做完,因为还有很多空白的地区。另外,泥沙的侵蚀量和输送量的差异量越来越大。所以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侵蚀泥沙没有被输送的,没有被长距离输送到海洋里的,它们是在什么地方—主要是在水库里,还是在流域里。这些也是正在做的工作。 记者:除了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泥沙项目之外,您还参与过联合国系统在中国开展的,或者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开展的与泥沙相关的项目么? 王兆印:我1995年一从德国回国,就参与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名字是支持黄河三角洲可持续性发展当时我们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黄河在河口地区是非常不稳定的。之前差不多每十年要改一次河道,大概已经改了十二次了。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把它稳定下来,否则黄河三角洲就没法发展。像长江三角洲是非常高密度的工业区,黄河三角洲就完全不一样,珠江三角洲也是非常繁华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它不稳定。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同时提出入海的河应该怎么来稳定住它,同时计划如何在未来的一百年,哪条河用多久,换另外一条河怎么做。就是通过人类的主动管理,使这个河按照我们要求的河道来走。但是自从我们做了之后,黄河实际上形式大变,一方面有我们做的工作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主要是上游的建水库和拦砂坝起了作用。黄河的泥沙剧降。所以我们做了以后,河就没有再动,只在1996年做了一个小的调整,在河口的河道那儿,有很小的一段儿,是为了把一个油田淤出来。那么大的河,因为黄河到河口那儿有很多河道,每一个河道有一个名字,有十几个名字呢。到河口就不叫黄河了,就叫清水沟了,它实际上就是黄河。现在清水沟已经用了30多年了,已经远远长于过去使用河道的时间,超过好几倍了,但现在看起来还能继续使用几十年。另外一个是当地的民众,通过这项活动,对于环境生态保护有了很大的觉醒。所以现在黄河口有个自然保护区,老百姓也自觉地加入里面的一些工作。 记者:作为一位泥沙运动规律方面的专家,在中国除了黄河流域之外,您还关心哪些地区呢? 王兆印:我过去在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关心黄河和三峡,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的大工程都在那里。现在,从90年代开始,主要精力投入到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研究。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有90%的资源,包括水电和其他资源,还有90%的生态和90%的景观。现在在西南地区的开发究竟对生态有多大的影响,我非常关注。最近,我刚刚去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沿路都是崩塌,走的路是非常陡峭的,差不多每一步都要小心地迈。而一天在山道走28公里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们在那里有很重要的发现,比如,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里,是最陡峭,水流最强,能量最大的地方,完全没有推移质运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因为根据传统的推移质运动理论是,水流强度越高,剪切力越大,垂直运动应该越强。但是那里没有。而正因为不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峡谷的稳定条件。如果进了推移质,它就会把大峡谷像拉锯一样拉下去。而现在这么陡峭的两岸会不断地崩塌和滑坡,那就是非常灾难的了。这么多年,可以说从Holocene, 全新世以来,推移质已经不再进入大峡谷了。有两个原因。一是它里面发育了一种结构,把能量全部消耗了。所以我们在研究它到底能消能多少,这样能保护大峡谷不让卵石进来;第二是这么多的卵石到哪里去了。我们做了一个测量,它们实际上都在上面的缓坡段,堆积了上百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可以颠覆我们传统的泥沙理论。所以我们从理论研究方面也非常关注它,而从开发大西南和生态角度来讲,我们也非常关注它。它要开发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上面采样,发现了一些物种。比如说无脊椎动物,在其他河流都没有找到的,那里找到了几种非常特殊的。当然,它对生态到底有多大影响,多大的作用,我们还在做研究。 记者:曾经有人说过,中国有两条黄河,一条是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一条是中下游河水相当浑浊的长江,您如何评价这种说法?三峡工程中的水库,是否又会因为长江当中的泥沙,很快被淤积呢? 王兆印:这个问题很好,但是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刚才讲了,中国的河流都在减沙。曾经有人说长江也将成为黄河,那个时候可能带有哗众取宠的意思,可能当年稍微高了一点。实际上,从长久的趋势上看,长江、黄河的泥沙从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下降。特别是到了90年后,下降得非常快。黄河的沙已经减少了80%,实际上入海的沙可能只有10%了,跟50年代到80年代相比。长江也是一样,减沙也非常剧烈。不算三峡,也是减少了一半;算上三峡,从上面下来的沙是非常少的。按照进入海的沙来算,也减少了75%以上。因此,长江并不是变成了黄河。而长江现在三峡以下有一段是很清的,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颜色。这个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会造成一些冲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三峡水库原设计390亿立方米,其中有170亿是用来淤沙的。根据过去的计算,这170亿泥沙要淤满的话,需要120年到150年。到了120年之后就会达到一个平衡阶段,来多少沙,走多少沙,不会再增加淤积量。根据三峡蓄水8年之后的情况来看,现在的淤积速率比预计的要低得多。这主要原因是上游来沙大量减少和采砂。我们做了一个统计,采砂总量可能会有一个亿。长江一共有5个亿的沙,光采砂就去了20%。这些采砂主要是城市建设所需用沙的材料。三峡水库就算这170亿全淤了,还有220亿的调节库容是不会变的。因此三峡是一个千年万年的工程,不会几百年就淤满。 记者:除了您刚才提到的采砂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造成了黄河和长江当中的含沙量减少了? 王兆印:咱们就说长江减沙吧。长江减沙有过研究,气候的变化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各大小水库加在一起量很大,估计有40%,使真正进入长江的沙减少了,植树造林能够起到20%的作用,剩下的就是采砂等其他原因。 记者:最近这几年,云南、甘肃等地方连续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泥石流事故。政府在做哪些工作帮助当地的民众进行长期的防范呢? 王兆印:中国的泥石流主要发生在四川、云南、甘肃和西藏。云南和四川的人口密度比较高,所以关注的也比较大。国家做的工作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控制侵蚀,像长防林工程,做植树造林;第二是做工程防治,主要有三种。一是谷防坝,在山谷里做些坝,抬高侵蚀基准面,减少侵蚀量。二是排导槽,来了泥石流,沿着沟走,绕开村庄和农田,排入江里。三是渡槽,保护铁路和公路,山中出来的泥石流,遇到公路的时候,要从空中过去,这样公路就不至于受损。其中,当然是谷防坝最主要。在云南的小江流域,沿城有107条泥石流沟。当地政府主要的治理方法就是建谷防坝和植树造林。建谷防坝和植树造林很有效,现在大部分沟都给制住了,有的沟基本上多年不发了,所以建起了村庄来。但是甘肃舟曲的泥石流是非常意外的,因为它属于特大泥石流,方量超过100万方。它也有谷防坝,但是谷防坝和排导槽只能防治一般的泥石流,对特大泥石流是无效的。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对特大泥石流的防治方法,主要是通过城镇布局躲避一下。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用了一种消能结构来防治特大泥石流。2009年我们做了实验,在四川震区绵远河上有个叫文家沟的地方。沟里发生了非常大的滑坡,所以泥石流都是滑坡提供的固体物质。2008年发生了非常多泥石流,死了很多人。2009年我们就在沟里做了消能结构—接替伸展结构。水流过的时候它的能量就被消减了,它就无法掏刷,无法将泥沙运动起来。所以2009年我们制作了接替伸展结构之后,全年没有发生泥石流灾害,尽管降雨量比2008年还大一点。到了2010年,当地政府按照常规的方法做了20个谷防坝,把我们的接替伸展结构拆掉了。因为是特大泥石流,暴雨很大,水流能量极高。本来谷防坝对一般泥石流是有效的,但是无法阻挡特大泥石流。结果一场泥石流将20个谷防坝全部冲毁,埋了村庄,死了12个人。这个对比说明,在特大泥石流的防治上必须考虑消能问题。消减它的能量,甚至比拦挡更重要。但是要让决策者认同甚至应用它,恐怕还需要10年的时间。我们正在做这个努力。但是目前有一个缺点,比如施工队伍不知道如何施工,没有施工规范,因为这种方法是全新的,他们掌握不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正在做研究。 记者:在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贝壳类的海鲜是不能吃的,因为在河流和沿海地区的底泥遭受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这种说法您是否同意呢?中国政府在治理河流入海口的底泥污染问题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 王兆印: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分地区来看的。比如说泥沙会吸附一些重金属,所以底泥里的重金属含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所以说所有的海鲜都不能吃的说法太笼统,绝大部分应该都是可以吃的。可能有个别地方污染比较严重。我们做了一个工作,从长江的中下游河口采了底泥,上层和底层的水样以及底栖动物,主要进行重金属的测量。我们发现,水里的重金属含量是最低的,泥里是最高的。在底部生活的底栖动物身体中的重金属含量是次之的。捕食底栖动物的鱼类是更次之的。食浮游生物为生的鱼类就更低一点。但是水里是最低,因为一下子就流过去了,水里面有一点就会在底下聚集。因为它是沿着食物链有个转移。有人说,转移到最后的环节是最高,是错的。从我们研究的结果来看,重金属沿着食物链传递的时候,传递一阶就会减少一点。越传越低,并不是越传越高的。贝类当然属于底栖动物,比底泥的重金属含量要低一个量级左右。人吃了之后,当然消化吸收的会更少一点。但是底泥(重金属)达到多少的含量就不能食用,国家应该出台一个管理的方法。但是笼统地讲,这些都不能吃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以上是联合国电台记者黄莉玲采访美国土木工程协会2011年度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获得者、清华大学教授王兆印。 本文从联合国网站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chinese/下载(IAHR中国分会秘书处2011-8-17) |
|
|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ydro-Environment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 China (Mainland) Chapter |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土木工程协会将2011年度的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颁给了清华大学教授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泥沙项目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王兆印。这是美国土木工程协会首次将以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长子、流体动力学家汉斯・阿尔伯特的名字命名的这一奖项颁发给一位中国人,以奖励王兆印教授对高含沙水流、泥石流、植被侵蚀动力学以及流域管理等方面认识的特殊贡献。联合国电台记者黄莉玲对王兆印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谈了有关中国的河流治理和泥石流等问题。王教授首先谈到了这次获奖的感受。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土木工程协会将2011年度的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颁给了清华大学教授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泥沙项目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王兆印。这是美国土木工程协会首次将以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长子、流体动力学家汉斯・阿尔伯特的名字命名的这一奖项颁发给一位中国人,以奖励王兆印教授对高含沙水流、泥石流、植被侵蚀动力学以及流域管理等方面认识的特殊贡献。联合国电台记者黄莉玲对王兆印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谈了有关中国的河流治理和泥石流等问题。王教授首先谈到了这次获奖的感受。